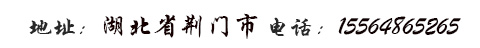台湾文学专家梁燕丽杨牧的诗想空间澎湃在
|
原创梁燕丽复旦青年 年3月13日,杨医院。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,杨牧留下了十四本诗集;而学者、翻译家、诗人三重身份合于一身,更让杨牧的诗歌融汇世界文学的深厚传统。因此,每一本诗集的出版,都拓展了汉语诗歌的潜能,甚至革新了诗风。向阳、陈义芝、陈黎等中生代诗人,俱笼罩在杨牧的影响下。无怪乎奚密许其为“现代汉诗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”。 阅读是对诗人最好的纪念。虽然杨牧的精品数量之多,无出其右,但许多仍不为内地读者所熟知。惟有多角度的阅读,才能领略杨牧多变的风格和博大的内涵。是故,我们邀请台湾文学专家梁燕丽教授,带领我们深入杨牧瑰丽的诗想空间。在本文中,梁教授独具只眼,用优美的语言揭示了古典文学、异国文化、国族历史、自然情怀等脉络如何在这个空间中交相辉映。 梁燕丽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:中外戏剧、台港澳文学、世界华文文学 ▲杨牧/图源国艺会网站 杨牧(-)生于中国台湾花莲,美国柏克莱大学比较文学博士,曾任华盛顿大学教授,旅美多年之后,回到台湾东华大学等校任教;作为著名诗人、散文家,兼具文论、翻译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,读者遍及世界华人圈。比较文学博士教授,杨牧创作以外,学术著作颇丰。诗人杨牧名副其实学贯中西,从西方古典到中国先秦典籍皆有心得。在杨牧看来,希腊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是自成一格的大传统,“我喜欢学问或诗,就会想去研究,去了解,去分析”。[1]由地中海回到中文世界,“我可以从荷马一头栽进左思或谢朓……这是两种传统,虽然我没有野心‘调合’之,但我可以让自己‘调适’”。[2]杨牧欣赏北宋欧阳修和南宋朱熹,诗文创作和问学相得益彰。杨牧本人既写现代诗也写古体诗。他说自己写现代诗时,很少会想到用典故,用的是一种思想模式;可是如果要写一首诗寄给朋友,可能就写律诗,可能从第二句就开始用典。然而白话文毕竟是现代人的写作工具,杨牧自述:“我到哪里都提细读古文,可是就写作而言,我相信唯有白话文可以依靠”。外文系出身,杨牧做翻译就像蒲伯(AlexanderPope)和柯律治(SamuelTaylorColeridge)一样,主要因为训练使然;同时信奉纪德讲的“任何懂外文的人,都应该为他的民族至少翻译一本书”。杨牧一生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罗尔卡(FedericGarciaLorca)、爱尔兰诗人叶慈(W.B.Yeats),以及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济慈等人的作品。从19到20世纪,阿诺德(MatthewArnold)、叶慈(W.B.Yeats)、艾略特(T.S.Eliot)等对杨牧创作影响最大。杨牧赞赏做现代主义实验的人,并且自己也是一个现代诗的实验者。杨牧的诗文,源自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,亦浸润西方文化之生命义理。在此,从生命淬炼和诗想空间,异国情调和国族寓言,自然生态和生态寓言,三个角度解读杨牧一些诗作,致敬杨牧一生繁复多样的创作和贡献。 ▲年,杨牧高中毕业,从花莲迁居台北,与台北诗人交游。左起:王渝、余光中、覃子豪、杨牧。/图源杨牧数位主题馆 一、生命淬炼和诗想空间 杨牧诗作对生命本真的抒写,质朴而灵敏;浪漫主义的抒情,来自心灵国度之美,以及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。在《有人》的后记,杨牧如此诠释诗的抒情功能:“即使书的是小我之情,因其心思极小而映现宇宙之大何尝不可于精微中把握理解。”作为纯情而唯美的游子,杨牧的诗属于生命淬炼或诗想空间?亦真亦幻,如梦似醒,这涉及最美的创作是生命觉悟或白日梦幻的发问,或许二者并没有真正不同,读者亦可多层面接受和理解。以《水之湄》、《雷池》、《雪止》、《暖日》等诗为例,足见生命淬炼和诗想空间的双重映像。《水之湄》: 我已在这儿坐了四个下午了 没有人打这儿走过——别谈足音了 (寂寞里——) 凤尾草从我裤下长到肩头了 不为什么地掩住我 说淙淙的水声是一项难遣的记忆 我只能让它写在驻足的云朵上了 …… ▲《水之湄》,台北藍星詩社年出版/图源杨牧数位主题馆 等待爱情或理想,四个下午,很具体的时间,攒足了孤独,却依然执着。“足音”表现等待者的专注,聆听足音,期待君临,但仍遥遥无期。“凤尾草从我裤下长到肩头了”,身体已被杂草淹没,用自然物象表征等待的心理时间之漫长,或者物理时间不止是四个下午,而是一整个春天过去了。“淙淙的水声”,表明等待的环境在“水之湄”,逝者如斯夫,一种无以排遣的愁绪,唯有天空飘过的云朵可鉴(我用诗句书写),艺术铭刻人生困境和韶光流逝,敏锐捕捉生命体验与想象,以诗留痕生命足迹,呈现时空限制和心理张力。《雷池》更将“时间―影像”凝结在稍纵即逝的瞬间,爱情若有若无,却叫人又惊又喜,只有诗的见证,使不可见的时间成为可见,使不可知的心灵颤动成为可知可感。“我们”宿命相遇而萌生的爱意和意趣,种种欲迎还拒、欲拒还迎的悲喜和忧思,如此复杂的感情凝练为单纯而隽永的画面: 我们像搁浅的小舟被吹在一起 羞涩地招呼着却不敢相识 怕――怕潮来时又把我们 送回那失去方向的大河 思念于忧伤怕不如淡忘于孤独的航行, 于风波的隐喻于一生的期待, 一点惊喜于一次不可能重逢的遭遇 《雪止》一诗生发的种种感情信息,从意识到潜意识,在遥远的梦土传来腊梅的暗香中,触及得更深、更含蓄、更浓烈: 我不能不向前走 因为我听见一声叹息 像腊梅的香气暗暗传来 我听见翻书的声音... 你的梦让我来解析 我自异乡回来 为你印证晨昏气温的差距 若是你还觉得冷 你不如把我放进壁炉里, 为今夜重新生起一堆火 “雪止”与“新火”两个相反相成的自然意象,构成“抒情沈静”的内在意蕴,诗人心目中真爱纯洁无暇和飞蛾扑火的形象。思念如潮,感情的困境顷刻化作重生之火焰。纯情唯美的艺术家,诗是抗拒现实的工具。在诗中生命之流得到自由释放,美学范畴亦达致最纯粹极致的实现。《日暖》已臻完美,日暖时节爱情如春花绽放: 随我来,蔷薇笑靥的爱 云彩雕在幻中,幻是皇皇的火 照你的长发,照你榴花的双眸 蔷薇在爱中开放,爱是温暖的衣 依旧,依旧是轻轻的雷鸣,宣示着 一则山中的传奇,水湄的神话 日暖时,随我来,让我们去坐船 小小的江面罩着烟雾 短墙上涌动一片等候的春意 林中有条小路,一段绿郁的独木桥 日暖时,让我们去,带着石兰和薜荔 走入雾中,走入云中 在软软的阳光下,随我来 让我们低声叩问 伟大的翠绿,伟大的神秘 风如何吹来? 如何风吹你红缎轻系的 长发,以神话的姿态 掀撩你绣花的裙角? 随我来,日暖时,水湄是林,林外是山 山中无端横着待过的独木桥[3] 从主观抒情到感性形象,在明媚春光中笑容如蔷薇,眼睛如榴花,云蒸霞蔚、如火如荼;你我带着石兰(春兰)和薜荔(木莲)行在画图中。“蔷薇在爱中开放,爱是温暖的衣”,爱是尽情的燃烧、温暖的守护;轻轻的雷鸣,则宣示“一则山中的传奇,水湄的神话”。我们一起去坐船,江面烟雾笼罩,矮墙上涌动着积蓄已久的春意,走过林中小路,跨过独木桥,抵达理想之境;人化入自然,活在自然万物生生不息中。日暖花开时节,请跟我来,所有爱与信任,交付于我。春意盎然、绿意盎然,人在大自然中生命勃发。如此纯粹的爱和人性,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。初看杨牧的诗写尽生命淬炼的“诗生态”,细看或是“纯粹性”探求的诗想空间。将现实的理想渴求升华为人文修炼,沧桑的笔调探触现实与理想的关联,以深化自己艺术生命基点。杨牧的诗,无论是自然的或抽象的,现实的或梦想的,诗人勾勒点染的图像,总能给读者穿透性的想象空间。唯有诗可以滤除生命杂质,提纯人文风范;历经心灵形式的统合整理,将情感转化为抽象的质素结构,不仅筑就传奇性的想象空间,而且内蕴生命的淬炼,企及精诚和完美的真境,甚至超越自我的崇高性。诗人创造生命的或想象的吉光片羽,以诗作为心灵最终归宿与完成。 ▲年,杨牧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镇(Amherst)狄金森(EmilyDickinson)故居前/图源杨牧数位主题馆 大约年笔名由叶珊改为杨牧后,作品从个人生命表达扩展到国族现实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engweicaoa.com/fwcls/1089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打卡小众的黄花风铃木,位于佛山的西樵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