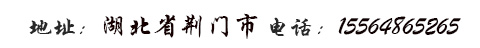ldquo兰妮子rdquo泣神动
|
『一咏』 大爱无言 图片说明:作者刘兰生的老父亲,一位厚道、勤勉而孜孜操劳红土地一辈子的淳朴农民。 爸爸去世一周年的那年清明节,我匆匆赶回故乡去给他扫墓。 重峦叠嶂的点梅坑里,春雨濛濛,溪水淙淙。我默默伫立在山腰间的爸爸坟前,禁不住泪如泉涌。墓地四周带雨盛开的杜鹃花,仿佛也洒满了我哀恸的泪水。 山无言,水无语,唯有相思鸟在松林里凄婉悲切地鸣叫着。 “爸爸,你见到了妈妈了吧?”我在心里泣问着。 微风轻轻吹过,宛如爸爸的喁喁细语:“见到了,见到了。” 爸爸终于结束了五十多年的相思之苦,同妈妈在那个冥冥世界相依相伴,永不分离了。 妈妈是在秋风萧瑟、落叶飘飞的季节里,因为生妹妹难产而死的。那年,她二十二岁,我才两岁。外婆说我长得像妈妈,可我总也想象不出妈妈的姿容。说实在的,在我记忆深处,妈妈犹如故乡山野间淡淡的晓雾晨岚,飘飘渺渺,朦朦胧胧。 但是,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我却亲眼睹了爸爸对早逝的妈妈的大爱,那么深挚,那么缱绻,令我刻骨铭心。 记得是六岁那年的早春,爸爸将我从山旮旯里的外婆家接回了古溪村。这年清明节,我跟随他 次去给妈妈扫墓。 妈妈的坟茔,坐落在樟排的松树林子边缘,两块竖立的青石,夹着巴掌那么大的墓碑,是农村里最简陋的那种坟。当时,野草青青的坟顶上露出两个碗口般大的窟窿。爸爸说,那是吃草的水牛踩塌了妈妈的墓穴。他嘴里喃喃着,去远处搬来几块石头将窟窿堵上,然后填满*土,植上草皮。 做完了这些,他悲郁地蹲在妈妈的坟前,轻轻地扒去落在墓地里的松针,轻轻地拔去墓壁上长着的凤尾草,仿佛生怕惊醒里头沉睡的妈妈。 挂完素纸,燃着线香,爸爸轻声叫我跪下来给妈妈作揖,他则提着那把陈旧的锡酒壶,缓缓地往墓前洒着水酒…… 祭奠完毕,爸爸带我在妈妈的坟前静静地坐了好久。我清楚地记得,离开墓地的时候,他泪光闪闪地抬起头,仰望着被松枝割裂了的天空,长长地叹息了一声,噙在眼里的泪水便顺着脸颊悄悄流淌下来。 那时候,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,不懂得爸爸复杂的情感世界,不懂得人世间生离死别的悲苦。但有一点我是晓得的:爸爸好想好想妈妈。 从此,每年清明节那天,我都跟随爸爸去给已故的亲人扫墓;每年去到妈妈的坟前,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总是最长,而且,爸爸的两眼总是泪汪汪的。 是妈妈去世第十三年的那个深秋,公社要修一条简易公路从樟排经过。好多人家的祖坟都得迁移。爸爸是生产队长,他自然得带头迁走妈妈的坟。 那天,当我从五里路远的固厚初中赶到樟排,正是残阳如血的时候。爸爸和道朋叔已将墓穴掘开,地下的两张红纸上,摆放着妈妈的遗骨和青丝。神情黯然的爸爸慢慢蹲下身子,从对襟衫上拔下一枚缝衣针,猛地扎破自己的中指,然后用力挤压着,任殷红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洒落在妈妈的遗骨上。 那时候,我不明白爸爸为何要这样做?后来我才晓得,爸爸破指滴血,是要表明生生死死都要同妈妈在一起呀! “东哥,起来吧!”道朋叔一边劝慰着拉起爸爸,一边将妈妈的遗骨和青丝包裹起来,装进了一只小谷箩里。 回到村子里,天早黑了,家家户户都掌灯做晚饭了。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,未满花甲的人,其尸骨是不能停放在本族祖堂里的。自然,那只小谷箩只能搁在祖堂门外竖立的麻条石上。 我现在总也想不起来,那天晚上我怎么会睡得那样沉?直到门外小巷里突然传来的一阵狗的狺狺狂吠,才将我从酣睡中惊醒过来。我和许多乡村孩子一样,一听见黑夜里的狗吠,心里便充满紧张、不安和惶恐,仿佛又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。我在被窝里颤声地喊着:“爸爸!爸爸!” 屋子里没有爸爸的应答声。我摸到了稻草枕头上的火柴,划着,点亮了条桌上的 灯。爸爸的床上空荡荡的,连被子也没掀开过。他去了哪儿呢?我的心不由怦怦地急跳起来。 近旁的周田上,传来婴儿的夜哭和母亲轻轻哼唱的催眠曲。住在池塘边小屋里的“小斋公”,也在楼上敲响了木鱼,开始了每天天亮前的念佛诵经。 有了人声,我的胆子骤然大了许多。我赶紧穿衣起床,端着那盏有玻璃罩子的 灯,走出深深的小巷去找爸爸。 爸爸坐在月色朦胧、霜冷风寒的祖堂门外,痴痴地望着那只小谷箩;小谷箩边点着一盏荧荧如豆的清油灯。当他扭过头来的一瞬间,我见他红红的眼圈里噙满了晶亮的泪水。 “爸爸,你一夜没睡呀?”我愣愣地站着问他。 爸爸用细细的芦基梗轻轻拨去灯草上结着的灯花,叹了口气,凄然地说:“你姆妈回家了,我给她点盏灯,照照路,陪她坐一夜。天一亮,她……又要走了……”爸爸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。 我的眼圈也湿润了。我去端来一张小板凳,坐在爸爸身边,同他一道默默地守着妈妈,守着一勾残月、满地寒霜。 东方渐渐发白了。不一会儿,给妈妈修坟的道朋叔和后森舅舅,也都按照约定的时辰来了。一夜未眠的爸爸,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,声音喑哑地对我说:“你去学校上早读吧,不要耽误了功课。” 几天后,我去看了妈妈的新坟。它坐落在深邃幽静的大山皱褶里,依然是两块竖立的青石夹着那块巴掌般大的墓碑。我知道,那时家里很拮据,爸爸实在拿不钱来为妈妈修一座稍微好一点的坟啊! 初中毕业后,我离开了故乡,去了县城读高中,去了省城读大学,后来又在城里工作,在城里安家。从此,我和爸爸关山阻隔,天各一方,再没有机会同他一道去给妈妈扫墓了。 这期间,爸爸信佛吃斋了。问起他的缘由,他说是芦莲排报恩寺里的一位老和尚告诉他,像妈妈那样年少死去的人,她的*灵还被关押在阴曹地府的水牢里,唯有爸爸替她吃斋念佛,方能将她从苦难中拯救出来,投胎再世。 当时,我只对爸爸苦笑了一下,什么也没说。 唉,我又能说什么呢?在那个工分值极低的年代,乡村里的农民,除了过年有点儿荤腥打打牙祭之外,平日里吃的几乎全是青菜、辣椒、腌菜、霉豆腐。因此,爸爸吃不吃斋我并不在意。在意的是由于他笃信了老和尚的点拨而变得神采奕奕起来,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慰藉。仿佛他把对妈妈的一腔情愫化作对冥冥佛界的虔诚膜拜,就当真能将苦命的妈妈从地狱中拯救出来。想想,我能忍心点破爸爸编织的那个凄美的梦幻吗? 也许,爸爸的虔诚果真感动了冥冥佛界,大慈大悲的菩萨终于安排爸爸妈妈在缥缈的梦境里相见了。 那是年的暑假里,爸爸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,进山探望阔别多年的舅舅和舅母。那天后半夜,跟我同睡一床的二表哥,几乎同时被一阵悲凉的哭声惊醒。 哭声来自睡在对面的爸爸床上。那是我 次,也是 的一次听见爸爸的哭声。 二表哥隔着蚊帐连声喊道:“姑丈哎!姑丈哎!” 爸爸应了一声,醒了。我问他为啥哭呢?他轻轻叹了口气,说:“我梦见你姆妈了。她就站在门槛边,盘着髻子,穿一身靛蓝布衫……” 当时,月亮落了,窗外黑漆漆的,有狗吠,有蛙鸣,有夜鸟在啼叫。我无法再入睡了,爸爸悲凉的哭声总在耳边回荡……那年,他已六十六岁,妈妈离开我们也整整四十三年了。 时间如白驹过隙,转眼又是八年。 进入年11月之后,爸爸多次托人捎来口信,嘱我抽空回去一趟,说是有事要跟我商量。商量什么事呢?他没说。 拣了个星期天,我驱车赶回两百公里远的故乡去。到家时,太阳离下山还有丈多高。爸爸不在家,邻居说他去*禾坑做事了。 翻上后山,走出青翠的松树林,*禾坑山岭上稀稀疏疏的红枫清晰可见。一群白鹭拍打着翅膀,从这片林子飞到那片林子,稍稍停留一会儿,又从那片林子飞向更远的林子。它们是在寻觅筑巢的好去处吧?冬天就要来了。 见到爸爸的时候,他正坐在山腰间松树荷树的荫翳下歇息,身旁垒着两堆高高的石块。仔细一瞧,他的衣裤和白发上,沾着泥土和草屑;一双皲裂得满是小豁口的手上,许多地方磨破了皮,或者结着紫红的血痂,或者渗出殷红的鲜血。 “你这是做啥呀?”望着苍老瘦削的爸爸,我又心痛,又纳闷。 爸爸微微笑了笑,说:“你姆妈的墓,以前建得太小了,我心里一直好难过。我想在今年冬至日,请人把你姆妈的墓扩宽一些,再换上一块大一点的石碑。” 我说:“给姆妈修墓当然好。但是,像撬石头、搬石头这样的重活,你怎么不请人来做呢?工钱我会付啊!” 爸爸凝望着远处影影绰绰的松林和村落,恬静地说:“这种事啊,自己做和请人做心意不一样。我都七十五了,我想啊,恐怕这是我在世上给你姆妈做 一件事了。” 太阳早落了山。暮霭氤氤氲氲,四野苍茫阒寂。一阵秋风掠过,浓密的荷树叶子飒飒作响。 下山回家的路上,爸爸指着距离妈妈墓地三百多米远的一个山坳,平静地说:“以后我过了背,就埋在那个地方。那里离你姆妈近,你回来给我们挂纸也方便。” 我久久无言,只觉得心里像针扎般的难受。 翌年初夏,爸爸突然病倒了。他患的是肺癌。我把他接到赣州,治疗、服侍了四个多月,终归是回天乏术。年3月25日,那个春雨潇潇的*昏,爸爸在故乡安祥地走了。他苦苦思念了妈妈五十多年,从此,他们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相依相伴,永不分离了。 爸爸去世之后的一年里,我不知多少回梦见他,也不知多少回从夜半的睡梦中哭醒过来。唯独扫墓归来的那天晚上,我才做了一个宽心的梦:仿佛是春和景明的早晨,爸爸扛着犁铧, 妈妈牵着水牛,他们一路说着,笑着,走过金*的油菜花掩映的阡陌,走过桃花嫣红李花雪白的溪畔,一直朝着晨雾缭绕的山垅里走去…… 图片说明:故乡春天的映山红,总是开得如火如霞。在作者眼中,映山红的霞彩里总藏着父亲与母亲温煦的笑靥。 提起父亲两个字,我就会想起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我的眼前则会叠印出罗中立的油画:那位满脸皱褶,裹着头巾,端着粗瓷碗的父亲,还会想起我自己的父亲。相比之下,刘兰生笔下的父亲,恐怕是今生带给我最多心灵震颤与慰藉,令我淌下最多泪水的父亲。 我曾给兰生发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engweicaoa.com/fwcyf/976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南区游学崇丽揽胜浣笺留韵
- 下一篇文章: 花样书单作家笔下的春天,你读过吗